卡爾維諾曾在《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》中寫道,「輕逸」的小說創作並非模糊、隨興,而是抵抗「沉重」的手段。香港這城市經歷大型社運、疫情及國安法實施,籠罩著陰暗的氛圍,偏偏自中學開始在學聯社運資源中心流連、05年韓農反世貿時已經上街、《少年》導演之一的林森,交出窩心溫暖的《窄路微塵》。它不處理甚麼城市論述或沉重的議題,只是訴說幾個小人物、幾粒微塵。
而且,這幾粒微塵尤其微小不顯眼,因為他們是在窄路之中懸浮——在香港,生活使人眼界狹窄、沒有消費選擇,就連物理上也屈居狹小的劏房。但在如此的空間裡,卻有「窄哥」這樣企直腰骨的人,便為「窄」字添了另一筆意義。就如《聖經》所寫:「你們要進窄門,因為引致滅亡那門是寬的」善良本質就是狹窄且不容易。
深刻地走進基層 刻畫無法言說的貧窮
《窄路微塵》講述張繼聰飾演的清潔公司老闆窄哥、和袁澧林飾演的年輕單親媽媽Candy,兩個萍水相逢的人如何在困境下掙扎求存。雖然同是天涯淪落人,但窄哥為人忠厚正直,Candy卻經常「走精面」。一次,Candy帶著女兒在便利店買雪條,她誤以為優惠期尚未完結,所以答應女兒,付款時才知道要付原價,於是趁店員不警覺時,悄悄把雪條放進袋裡偷走。
在深水埗長大的林森,刻畫貧窮基層的生活面貌時,沒有特地站在任何一方的位置。疫情下,Candy母女生活困苦,連交租也成問題,但是否因為窮就可以偷東西?畢竟,電影把她對照公司破產後同樣苦不堪言、但仍堅持原則的窄哥——《窄路微塵》沒有刻意同情基層,也非沒有站在道德高地批判Candy;只留下一大片難以定義的灰色兩難地帶,引發觀眾思索。
也許你認為偷雪條是不正確,但Candy第二次出手時,是在一間豪宅裡找到幾十盒小童口罩,她取走了兩盒。Candy回家後為女兒試戴,露出滿足表情:「你看多麼貼身!」、「不會漏氣!」Candy偷東西不過為了女兒健康福祉,想盡力做一個好媽媽。《窄路微塵》寫貧窮寫得深刻到肉,因為它反映出貧窮的多個面向:生活困頓固之然是,但原來這種困頓也牽連無辜的下一代,Candy偷東西只希望補償女兒。
此外,Candy母女衣著打扮光鮮漂亮,總是化妝與仔細地束起許多小辮子,也突破了普遍人認為窮人就衣衫襤褸的印象。雖然生活潦倒,但不代表失去對生活品味的追求,甚至快樂的權利,這也許是電影寫貧窮寫得最好的一筆。
狹窄生活中 擁有快樂的權利
生活使人狹窄,不單是眼界、心境、消費選擇,就連物理上也需要屈居劏房。沒有地方比香港更適合訴說升斗市民的故事,因為那種困厄與窘迫是可見的、可觸摸的、具象化的——在繁華鬧市裡,赤裸地買不起三十元雪條;在四面牆的劏房,連一扇可以透氣的窗都沒有。
《窄路微塵》拍了一些窄哥與Candy母女在街巷行路的大遠景,凸顯城市空蕩且大的空間;鏡頭一轉,便是從對面單位拍過去,影著賓館窗中兩母女的身影。鏡頭無聲地述說著,香港建築密集式地見縫插針,伸手即可觸及對面的窗,不留丁點私隱空間;同時,鏡頭把大廈外牆都收納畫面,顯得窗中的母女在一個長方形框裡,意味貧窮就是一個實在的框架,局限著小人物的生活。
縱然坎坷,但快樂是每個人的權利。當Candy母女被迫收拾細軟搬到賓館,她們透過單位唯一的窗望出外面的世界,舉手指著見到的植物、陽光。從絕處看到充滿朝氣的生命意象,也是林森為黑暗悲情的城市滲進一絲光線,寄語留在這裡努力的人意志頑強且堅靭。
要進窄門 為自己而做的善良
相比母女,窄哥的善良顯得比較超現實,既不貪心,安分守己,甚至不介意自己「蝕底」。相比「手腳唔乾淨」(「偷東西」的廣東話俗語)的Candy,做清潔工作的窄哥,顯得在道德方面尤其乾淨。
在這種意義上,清潔不單是賺錢的工作,更是一種修為,一種見到城市骯髒的污漬、便出手清理的功德。Candy曾經問窄哥「人生有甚麼意義」窄哥卻用清潔工作來回應:「清完又會髒,髒了又再清理。」完全地照見現實的殘忍。從結果來看,人生的確沒甚麼意義,所做的清潔工作僅維持一段時間,隨即又被污染;但窄哥並沒有因此質疑自己的努力,更認為因為世界不潔,所以更需要勤力清洗、消毒、除去污垢。
電影沒有解釋窄哥的名字由來,但也許「窄」字也代表善良的選擇。所以疫情肆虐也不會偷有錢人家的口罩;Candy和女兒害他公司破產,他也不計前嫌,塞錢給她們過生活——你或者不太同情他,一個如此蠢鈍的好人,為了善良而賣車、打工、把自己逼得窮途末路。但善良的本質就是狹窄且不容易,就如《聖經》所寫:「你們要進窄門,因為引致滅亡那門是寬的」。
《窄路微塵》最後一幕,是轉行做保安的張繼聰,深宵巡邏時見到地上有攤嘔吐物,忍不住出手把它清理。所謂善良的意義正在於此——沒有人見到你付出,沒有人答謝你;善良是為自己而做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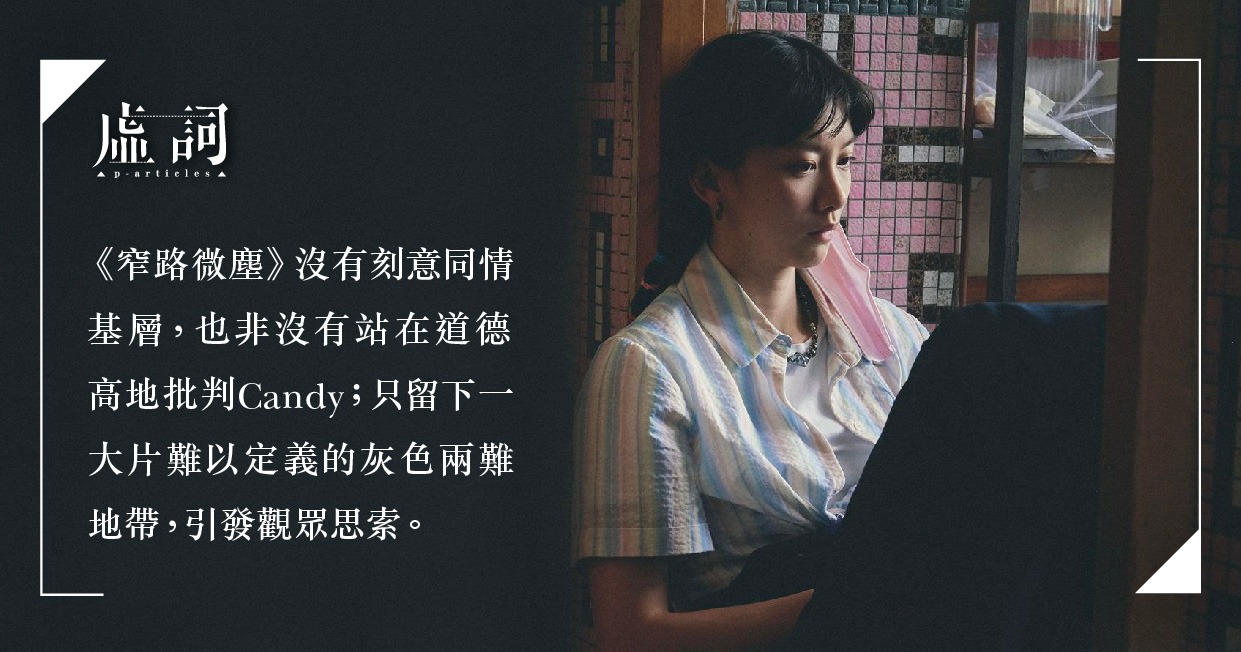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發佈留言